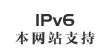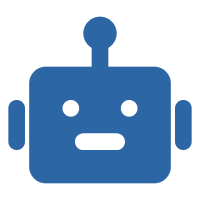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 每日动态
银川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yinchuan.gov.cn
来源:银川日报 2025-07-14 15:01
字体颜色:
[红]
[黄]
[蓝]
[绿]
保护视力色: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恢复默认

2025年7月10日在宁夏银川拍摄的西夏陵1号陵与2号陵(无人机照片)
当一缕夕阳为贺兰山脊镀上金边,九座黄土巨冢在戈壁长风中投下巍峨剪影。
当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聚光灯投向中国的西夏陵,这些夯土建筑群向世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不是单一文化的独奏,而是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依旧是贺兰山苍茫的背景下,一部西夏陵的申遗文本,摒弃空谈,深扎陵区,以考古实证为唯一语言,为西夏陵叩响世界文化遗产大门。
申遗正名与文明彰显
西夏陵的申遗工作,正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精神的深刻实践。对此,中国建设科技集团首席专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深总规划师、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深有感触,她回顾了建筑历史研究所过去20多年在世界遗产领域开展的实践,坦言:“早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匮乏令人惊讶,但伴随国力提升,经济崛起后,文化尊严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自信,更要将中华文明特质及其蕴含的古老智慧,展现于世界文明的舞台。世界遗产公约作为联合国影响力最广泛的公约之一,正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阐明文明内核的关键场域。
西夏陵的价值发现,尤为契合这一战略深意。陈同滨揭示了一个历史痛点:“二十四史中竟无西夏之名。”
她追溯蒙元史官托托修史旧事,猜测西夏史可能曾被纳入计划,却因蒙元与西夏复杂的历史纠葛,而最终缺席正史,成为一份历史的遗憾。因此,西夏陵申遗,超越了打造“文化金名片”的浅层目标,它在百年变局中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独特影响力。正如陈同滨所言:“当国际社会惊讶于中国有连续不断的文明时,西夏陵的存在正解答了这个疑问。”
从史料匮乏到实证破局
2011年11月23日,贺兰山下,一场启动仪式牵动人心。西夏陵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作为咨询单位,接过了这项“五维一体”的任务,即价值研究、保护规划、管理规划、遗址公园规划及博物馆设计。其中,陈同滨所在的建筑历史研究所作为牵头者,其职责不仅是规划编制,更要确保所有设计均服务于“揭示与传达遗产价值”这一终极目标。
真正的挑战,来自历史的沉默。“接到申遗项目前,我们并未特别关注过西夏时期。开始研究才发现,研究的人很少,史料也很少。”陈同滨说,西夏文文献的加密特性,导致可参考的史料不足辽、金史的十分之一。
这个于11至13世纪屹立在西部农牧交错带的王朝,疆域曾达115万平方公里,在脆弱的生态中,在宋、辽、金、吐蕃等强邻环伺的复杂地缘中存续了190年。党项人如何在严酷环境中,开创并维系此基业?面对史料,陈同滨团队确立了“用材料说话”的考古实证主义原则,从地面遗存中解读西夏。
团队驻扎陵区,对每一处遗迹进行测绘记录。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的分布规律,5万平方米建筑基址的结构特征,防洪系统的工程原理……这些一手资料成为文本的基石,也是解读西夏时期社会发展的关键物证。
经过多年攻坚,2024年1月,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遗文件。3月份收到格式检查合格通知,接着,价值研究评估启动。西夏陵终于站上世界文化遗产评审的舞台。
自然与人工双要素支撑世界遗产价值
价值阐释需要坚实载体。面对宏阔苍凉的西夏陵,陈同滨团队的首要任务是从庞杂遗存中提炼出支撑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核心要素。这如同为一位缄默千年的巨人绘制基因图谱。
早年间,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在良渚、故宫、敦煌、云冈等遗产规划的探索中,积攒了许多经验,深知遗产要素归类既要尊重实体遗存,又要体现自然与文化的有机互动。团队无数次穿行于贺兰山麓的帝陵与戈壁,反复勘察、测绘、研讨、修正。
最终,团队精准锁定构成西夏陵遗产价值的骨架——4个自然要素与4个人工要素。其中,自然要素包括贺兰山本体、山前的冲积扇地形、冲积扇上方的戈壁荒漠景观,以及扎根于戈壁滩上的花木植被。这4项自然要素绝非背景板,它们深刻参与了陵址选择、建材获取、防洪设计乃至精神象征的构建。
人工要素包括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32处防洪系统遗迹,以及5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群,它们构成了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重大遗存。
3389公顷的史诗
贺兰山,以铁铸般的嶙峋脊梁,巍然横亘于荒漠戈壁与塞上平原之间。它是中国地理二级阶梯的天然界标,也是西夏陵的壮丽背景。贺兰山前冲积扇是遗产生态基底的核心构成。这一扇形地貌由山洪冲刷形成,创造了西夏陵独特的台地环境。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星罗散布于山脚下,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的洪积扇戈壁上。
在申遗文本中,贺兰山是解读中国西北地区地貌演化的关键剖面。冲积扇的纳入,揭示其多重价值:地形上,它分割出陵区四大自然区块;生态上,戈壁滩与荒漠植被在此交错。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发布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遗产区的划定,要完整包含遗产本体及相关环境要素。“我们将山脚沿线、银阀公路、110国道之间的3389公顷的面积,划为遗产区。”陈同滨说,冲积扇不适宜居住,原始地貌上没有建筑压力,避免了建设性破坏。
但遗产区与缓冲区在划分时,还是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要处理好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405.69平方公里的缓冲区,除了完整包含遗产环境要素,还要能够抵御城市开发的潜在压力。“当时国际专家提出过疑问,为什么划界这么大。其实就是担心该区域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我们解释说,这是一个完整的视线环境保护区域。”陈同滨说,贺兰山轮廓线是遗产精神感受的组成部分。当你站在那里,视野中没有现代城市痕迹抢夺自然的雄浑,一段苍凉的史诗便在心中唱响。而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能力,足以支撑这一划界。
西夏陵申遗文本中的自然哲学
冲积扇孕育的戈壁滩、荒漠景观,是西夏陵最具冲击力的自然要素。申遗团队在价值论证中提出“不宜绿化”的保护哲学:裸露的砾石地表并非生态缺陷,而是党项人在脆弱环境中存续190年的见证。陈同滨以现场经验强调:“若为美观种植花草,将彻底破坏遗产的原真性。”
这一理念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得到印证。夕阳将戈壁染为金红时,陵塔的夯土轮廓与山体阴影形成史诗性对话。文本中纳入多幅照片,展示了戈壁滩作为荒漠生态系统的一种类型,所具有的独特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
戈壁景观上的特有荒漠植被品种是西夏陵遗产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它们构成了脆弱生态的活态见证。在申遗文本中,团队特别强调了这些特有旱生植物的保护价值。
“一草一木都是历史层积的产物,克制干预也是保护。”陈同滨说,这些植物不仅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有花木品种,是千年自然选择的活态标本,其耐旱特性揭示了党项人生存环境的严酷。
9座帝陵的见证
西夏陵,这片位于宁夏平原坡地、贺兰山脚下的宏大陵墓群,见证了西夏王朝的历史。在申遗文本的编制过程中,陈同滨及其团队深入研究了西夏陵的核心价值。其中,9座帝陵作为最显著的人工要素,不仅展示了西夏王朝的丧葬制度和建筑艺术,还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陈同滨指出:“9座帝陵是西夏陵的核心,1、2、7、8号陵属A型,陵域有双重围墙;3、4号陵是B型,用角台标识范围,没有外重围墙;而5、6号陵则是C型,兼具角台和部分围墙的特征,像是前两者的融合。”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帝陵在选址、布局、形制上均体现了党项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创新。团队在文本中详细记录了这些发现,“西夏的陵寝制度,与唐宋陵寝制度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
271座陪葬墓的社会结构密码
除了9座帝陵外,西夏陵还分布着271座陪葬墓,这些陪葬墓在规模、布局、随葬品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异。陈同滨团队在编制文本时,对这些陪葬墓进行了详细分类和统计。
“陪葬墓的等级差异直接反映了西夏时期的等级结构。”陈同滨解释道,“大型陪葬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多为贵族或高官所有;而小型陪葬墓则相对简陋,多为普通官员或平民所有。”通过对陪葬墓的研究,团队不仅揭示了西夏的等级制度,还发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陪葬墓的分布也耐人寻味,“自然冲沟将墓区划分为四块,其中中部区域(5、6号陵附近)密集分布着118座,远超其他区域,可见这是个非常鼎盛的时期。”陈同滨说。另外,出土的牛、马等牲畜遗骸,也诉说着这个位于农牧交错带上的王国,兼容并蓄的生计方式。
西夏陵的防洪系统是其另一重要人工要素,共有32处防洪系统遗迹分布于陵区各处。陈同滨团队在考察过程中发现,这些防洪系统大多由石块、夯土等材料构成,设计巧妙、结构合理。“防洪系统的存在说明党项人非常注重陵墓的长期保护。”陈同滨表示,“他们通过科学规划和建设,确保了陵墓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在文本呈现上,团队采用了图表、照片等多种形式,直观展示了陪葬墓的分布情况和等级差异。对于陪葬墓中出土的文物,团队也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解读。同时,详细记录了防洪系统的分布位置、结构特点、功能作用等。这些内容为人们了解西夏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破解谜团 为历史正名
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是一处占地约5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基址群,其规模之大、布局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关于该建筑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给守陵人的居所。”陈同滨说,团队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比对,发现建筑群中出土的石像残件与中心大殿的布局,均符合祭祀场所的特征,而非此前猜测的守陵居所。这一发现不仅终结了长期以来的争议,也为研究西夏陵的祭祀制度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帝陵区一座陪葬墓边上,一个巨大的坑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当做一个‘盗坑’,但若真是‘盗坑’,它在文本中该如何呈现?对我们申遗是否有影响?”陈同滨说,一般盗坑约有50公分,而眼前这坑几十米宽,不大像是为盗墓而挖的。再结合历史背景,蒙古灭西夏的过程,以及蒙古军队破坏敌手陵寝的记载,由此推论:这个巨坑极可能是当时元军有组织的泄愤行为。因此,申遗文本将此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呈现出来,是西夏王朝悲剧性终结与蒙夏关系惊心动魄的历史见证。
西夏陵诠释世界遗产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共有6条,在西夏陵的申遗文本中,主张其符合标准二(展现出某个时间跨度或世界某个文化区域内,有关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发展之人类价值观念的重要变迁或交互影响)和标准三(能为传衍至今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提名地(西夏陵)在选址、空间布局、制度、建筑技术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这种交流。”陈同滨指出,西夏陵虽然学习了北宋集中陵区的选址格局,但在具体制度与布局上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例如轴线偏移、增设月城以及将石像生移入月城等。建筑上,独特的鱼尾形鸱吻和三号陵的弧形阙台转角,展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党项人其实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又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他们学而必改。”
此外,其宏大的陵寝遗存本身,从多个维度见证了西夏时期的社会发展,如社会结构、多民族构成、精神信仰、生业方式、文化成就(如自创的西夏文字)以及技术水平。
国际视野下的西夏陵土遗址保护
在价值论证的关键阶段,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专业考古发现转化为国际社会能理解的文化叙事。“还是那句话,用材料说话,某位专家个人的推测很少直接采用。”陈同滨说,面对国际评审严苛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标准,西夏陵的价值论证聚焦于文明碰撞的具象表达,文本也以多重物证构建西夏文明图谱。
为说服ICOMOS专家,申遗文本展开跨文明对标:纵向比唐宋辽金,横向比高句丽王陵。结论清晰:西夏陵以农牧文明交叉、多信仰融合的特质,填补亚洲陵墓遗产空白。“同期宋辽金陵墓都是垂直传承,西夏陵是多元创新。”陈同滨指出关键差异。
国际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对这些材料展现出显著兴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西夏陵作为多元文明交流融合的物证,如本土化改造的鱼尾鸱吻等构件,直观印证了跨区域文化互动;二是对中国土遗址保护技术的成效表示惊叹与认可,“国际专家对西夏陵在露天环境下历经几百年风雨仍能保持相对完好的状态感到‘惊诧’,并对我们的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
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

 首页
首页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 政务服务
政务服务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 了解银川
了解银川